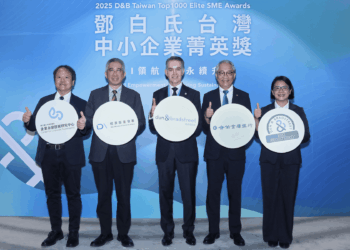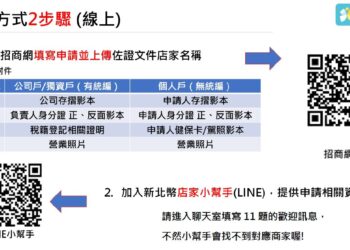文/李文煥 「我是客家人,但我不會講客家話。」這句話,筆者在台北求學時期不知聽了多少遍。起初,只覺得是個人經驗的巧合,漸漸地卻驚覺這是普遍的社會現象。尤其在雙北這樣的大都市裡,聚集了各地的移民,語言文化在都市化與現代化的巨輪下,被迫收斂與隱沒。當越來越多朋友自我介紹時提到「我也是客家人」時,那種久違的他鄉遇故知的情感總會浮現,但下一句「可是我不會講客家話」,卻讓人不知該苦笑還是心痛。
這並非筆者孤單的感受。一晃眼,二十多年過去,我也步入中年之年。回首同齡的鄉親朋友們,能說一口流利客家話的人,竟是屈指可數。更不用說七年級、八年級、九年級的年輕世代了。我的弟妹們,雖然耳濡目染可以聽得懂,但日常中卻幾乎不用母語溝通。說得少、用得少,語言就自然淡出生活;久而久之,連記憶也將消散於時間的長河。
母語的流失,並不僅僅是語言能力的喪失。更深層的,是文化的中斷與認同的淡化。一種語言的消失,往往伴隨著世界觀、價值體系、生活智慧與集體記憶的失落。語言並非只是傳達訊息的工具,更是承載文化與身份的容器。
客家話的失語,並非一夕之間發生,也並非哪一代的錯。我們不能責怪年輕人不會講,也不能僅僅哀嘆老一輩走了語言也跟著走。必須追問的是: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,我們是否曾經努力過去保留與傳承?在我們這一代是否堅持在家庭中說客語?是否讓孩子從小熟悉自己的語言?抑或我們早已妥協於「說國語比較方便」、「客語不重要」、「講母語會被人笑」的扭曲價值觀?
這個問題不只是客家人面對的問題。原住民族語、台灣台語、甚至新住民語言,都面臨類似處境。多少人說:「我是排灣族,但我不會講族語。」「我是台灣人,但我袂曉講台語。」「我是越南新二代,但不太會講越南話。」語言的斷裂,在今日的台灣已然是跨族群的普遍現象。
然而,我們不該也不能就此認命。語言的復振,雖非易事,但也並非不可能。政府早已看見這樣的危機,陸續制定了《國家語言發展法》,鼓勵族語教育、製作母語教材,甚至納入校園課綱。但制度的力量,若無家庭的配合、社會的氛圍支持、個人的行動選擇,也難以真正落實。
語言的生命在於使用。不是在學術論文、政府報告上活著,而是在廚房、客廳、菜市場、早餐桌上活著。我們是否敢在生活中開始說母語?哪怕一句、兩句,也是一種起點。語言不能只等孩子在學校學,而要從家庭裡自然成長。孩子若從小就在耳邊聽見母語,就會自然產生語感,這是任何課堂學習無法取代的。
客家話,是筆者的母語,也是一種情感的歸屬。每當在苗栗的街頭巷尾,聽見長輩們親切的問候,內心便有說不出的溫暖。這不是文言文的典雅,不是普通話的標準,而是一種從骨子裡牽動你靈魂的聲音。試想,有一天,當我們的孩子再也聽不懂長輩的話語,甚至無法和自己的祖父母用一種熟悉的語言溝通,那將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?
筆者始終相信,語言不是傳統的包袱,而是文化的禮物。我們不能只在表格上填寫「我是客家人」,卻不願在嘴裡說出一句「食飽吂?」我們不能只在節慶上穿上族服跳舞,卻平時不說一句族語。我們更不能只在問卷調查上表示「支持母語教育」,卻從不在生活中實踐。
是的,我們都很忙,生活很累,講母語不是效率優先的選項,但它是我們為孩子、為文化、為自己的根所做的一份承諾。讓我們從今天開始,無論你是客家人、學佬人、原住民或新住民,在家裡、在生活中,多講幾句母語。不要怕講得不標準,不要怕孩子聽不懂,只要開始,語言就會活起來。
「我是○○人,我會講○○話。」讓這句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驕傲,而是每一個台灣人都能大聲說出的自信與文化自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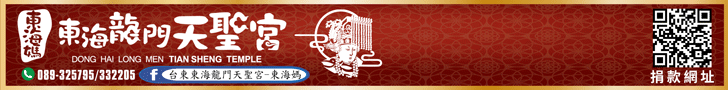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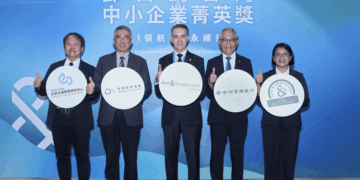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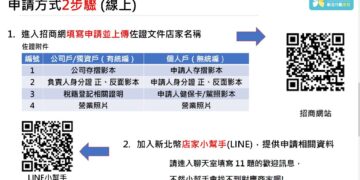



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4416117_122148183224564414_2022793461796062593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75124989_122138600534564414_5098057897882802451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下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打造專屬成功模式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5825496_122150271926564414_9054305621568034742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962107_122147791340564414_6695923268119771423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邀約到場不是結束,而是成交的開始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024255_4003090606632661_4408849211036270947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想賺錢卻不想學?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1820331_122146449434564414_9052605497599197724_n-360x180.jpg)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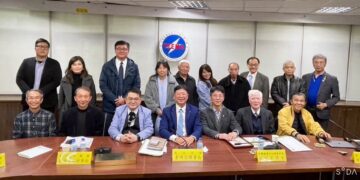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公民幫推協會理事長黃建興、前馬來西亞檳州行政議員鄧章耀、清福醫院院長王炯琅、中華生技醫藥行業協會理事長陳建州藥師--360x180.jpg)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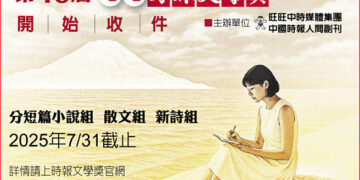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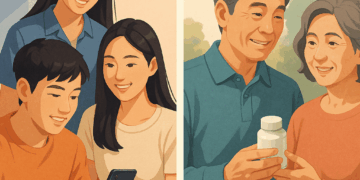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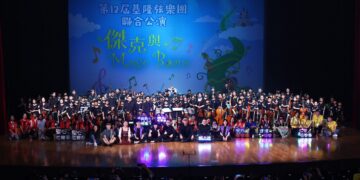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