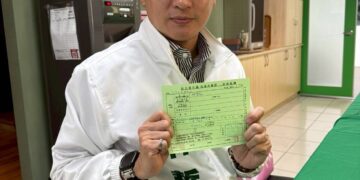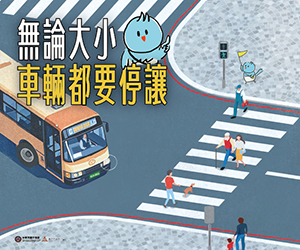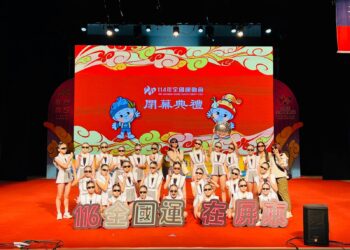文/李文煥
在我國的中小學教育現場,對多數學生而言,課本只是書包裡的一本教材;然而,對視覺障礙、學習障礙、聽覺障礙、智能障礙乃至腦視覺障礙的學生而言,這本教材卻往往成為學習的第一道阻礙。當教材僅以紙本或掃描影像 PDF 形式存在時,不僅視障生的螢幕報讀器無法正確辨識,學障生也無法結合語音輔助進行閱讀,聽障生更缺乏多模態支持,專注困難或智能障礙學生也難以調整學習方式。教材形式的單一化,直接造成教育不平等。
筆者在國立臺南大學博士班修讀「全方位學習設計」(UDL,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)課程時,深刻理解到一個理念:好的教材設計,並不是為少數人事後加裝輔具,而是從一開始就建構一個所有學生都能使用的環境。若教材依循通用設計原則編製,不僅視障學生能透過螢幕報讀或點字顯示器同步學習,學障與閱讀障礙學生亦能使用 TTS(文字轉語音)與易讀模式減輕負擔;聽障學生則能藉由多媒體字幕與圖像輔助獲取內容;專注困難或智能障礙學生也能因個人化的調整模式受惠。這樣的教材,不再是「替代檔案」,而是所有學生都能同時使用的學習工具。無障礙只是最低標準,而通用設計才是教育品質的進階保證。
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(CRPD)第九條與第24條明確指出,教育應以「無障礙」與「包容」為核心,保障人人平等取得資訊。若國家與出版商仍停留在紙本或不可讀 PDF,等同制度性剝奪障礙學生的學習機會,不僅違背國際人權規範,也忽視教育公平的根本。臺灣早已有法源基礎。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與《著作權法》都已排除版權疑慮,明確賦予教材無障礙化的正當性。然而,在實務運作上,家長與學生仍必須一再申請電子檔,卻常遭出版商以「技術限制」為由推託。這種「事後補救」的做法,不僅效率低落,也使平權保障淪為形式,學生依舊被迫落後。
國際經驗早已證明教材的無障礙化與通用設計並非不可行。美國依據 ADA 與 IDEA,要求出版商同步提供數位無障礙教材,並由州教育廳設立統一平台,讓合格學生能直接下載,免除繁瑣申請。日本則透過《教科書無障礙化推進計畫》,明訂出版商必須在教材出版當年度同步產出 DAISY、Word 與可報讀的 PDF,違反者甚至失去下一年度供應資格。歐盟更透過《無障礙法案》(European Accessibility Act),將電子書的無障礙設計納入法律義務,推動出版產業全面轉型。相比之下,臺灣在制度設計上仍顯滯後。
教育部若能在國小、國中教科書共同供應契約中,明訂出版商必須依循 WCAG 2.1 AA 標準,製作可存取的 Word、Tagged PDF 與易讀模式,並集中於中央統一平台上架,不僅能大幅減輕家長與學校的行政負擔,更能真正落實教育平權。更重要的是,這樣的政策方向必須超越「視障專用檔案」的補充,而是全面提升教材設計理念,邁向通用設計。畢竟,教育現場的挑戰不僅來自視覺限制,還包含學習差異、感官缺陷與專注困難。當教材以通用設計思維出發,它的價值不只是「平權」,更是「優質教育」的重要一環。
通用設計教材的最大意義,在於創造「無差別的可及性」。對視障生而言,它意味著能隨時放大字體,或透過點字顯示器觸讀內容;對學習障礙與閱讀障礙學生而言,它意味著能結合語音朗讀,減輕閱讀壓力;對聽障學生而言,它意味著能搭配字幕、圖像與符號輔助,理解課文重點;對智能或專注困難學生而言,它意味著能透過簡化模式與格式調整,獲得個人化支持。這樣的設計不僅保障「同步學習」,更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在同一課堂上共同進步。對教師而言,教材的多模態呈現,也有助於差異化教學與個別化支持,減少額外備課負擔。
值得強調的是,這並不是要求出版商無償提供服務,而是教育部應編列經費,制定嚴謹規範,並建立監督與品質把關機制。唯有如此,出版業者才有動力與能力投入,也才能確保教材品質。既然政府已推動「生生有平板」,那麼下一步就應該是「平板裡的教材人人可讀」。數位化的通用設計教材比起笨重的點字書更便於攜帶,成本甚至可能僅為後者的十分之一,但效益卻能惠及所有學生。這是一項高效益、低成本,且符合國際潮流的教育改革。
在資訊社會裡,教材的形式就是教育的入口。當教材被鎖住,教育的門就被關上;當教材依循通用設計原則開放,不只是視障生,而是所有學生都能受惠。臺灣不該再讓「障礙」成為藉口,而應以「通用設計」作為行動,真正打開教育無障礙的大門。教育的核心價值,在於每一個孩子都能平等參與學習。唯有通用設計教材,才能讓這個價值真正落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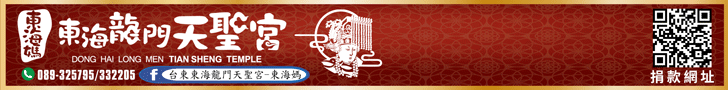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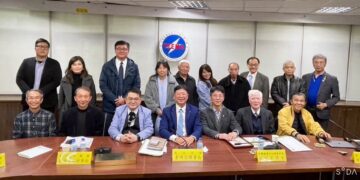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
-26-360x180.jpg)

-360x180.jpg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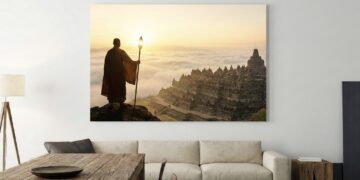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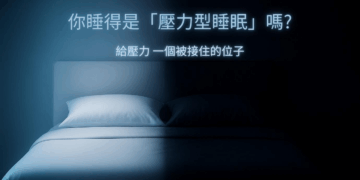





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