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李文煥
今天,本應是桃李芬芳、群生致敬的教師節,理應是歌頌師道、表揚教澤的日子。然而,台北街頭卻傳來令人心酸的一幕:一群年過半百的老師,頂著烈陽站在教育部門前,手舉標語,神情悲憤而無奈,向社會大聲疾呼,說這是「史上最黑暗的教師節」。多家媒體報導指出,教師節當天已有教師與聲援者走上街頭抗議,訴求校事會議制度黑箱、不公,甚至指其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。這一幕令人震驚,也引發社會對校事會議可能違憲的廣泛關注。
所謂校事會議,本是教育主管機關所設計的一套程序,其法源主要來自《教師法》第14至第16條,以及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》第12條。依據這些規定,一旦教師被學生或家長檢舉,學校便須召集校事會議,由校內外委員組成,包括校長、家長會代表、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會代表,以及教育學者或法律學者專家等。會議的職責是審查教師是否存在「不適任」情形。初衷看似合理,因為教育需要自律與外部監督,社會也擔心若教師有不當行為,學生卻無處申訴。
然而,制度一旦進入現實運作,便可能背離原設計意圖,逐漸演變成教師口中的「絞肉機」。檢舉往往可以匿名,證據不一定充分。教師被迫接受調查,甚至立刻停聘。整個過程中,教師不知罪名,也不知指控者是誰,卻被要求「自己證明自己無罪」。這樣的設計,使校事會議在操作上,幾乎等同於「先定其罪,再看能否翻身」。一夕之間,教師失去的不只是工作權與名譽,更是數十年教學生涯的積累與尊嚴。
台灣是一個以憲法為根本的民主社會,而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,理應毫不動搖。憲法第十五條明白指出,人民的工作權必須受到保障。教師若因未經證實的檢舉而被停聘、解聘,顯然就是對工作權的直接剝奪。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的正當法律程序權利,凡涉及重大利害之處分,應有告知、答辯與辯護的機會。然而在校事會議中,教師往往不知罪名、不知證據,辯護空間被壓縮。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尚未列舉之自由與權利,其中包括人格權與名譽權。教師一旦遭調查,即便最後清白,名譽早已受損,社會印象難以恢復。
更重要的是,「無罪推定」乃現代法治的根本。大法官歷來在釋字中重申,雖然「無罪推定」原則主要適用於刑事審判,但涉及人民重大基本權的行政處分,也必須遵守相同程序保障。校事會議若將舉證責任倒置,讓教師「自己證明無罪」,顯然已違背憲法精神。這種「有罪推定」在校園橫行的現象,豈是法治社會所能容忍?
有人或許會認為,這不過是學校內部行政調查,無須大驚小怪。然而事實遠非如此。校事會議的結論直接關乎教師的去留,決定一位老師能否繼續站在講台上,能否在社會立足。對教師而言,這已非小事,而是職業生命的裁判。一旦誤判,不僅飯碗不保,名譽盡失,甚至永無重返教壇之可能。當制度能輕易將人打入無底深淵,社會若仍視之為小事,教育根基必然動搖。在這樣恐懼陰影下,教師將不再敢嚴格教學,也不敢堅守原則。受害的不僅是教師,更是學生與整個教育環境。
再觀國際,他國制度雖不同,卻皆嚴守程序正義。美國要求教師申訴與懲處遵循「due process」,明確告知指控內容,允許聘請律師、交叉詢問證人,無具體證據不得停聘。英國設有獨立仲裁機構,教師可上訴,過程公開透明。德國教師屬公務員,懲戒須依公務員法程序,甚至需法院審理,不容草率。相比之下,台灣的校事會議閉門運作,程序不透明,教師無保障,落差令人憂心。當世界各國尋求教育與人權平衡,台灣卻落入倒退,將教師置於隨時可被犧牲的位置,實令人羞愧。
因此,我們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。校事會議現行設計已產生多處違憲疑慮,無論對工作權、正當程序、名譽權的忽視,抑或對無罪推定的顛覆,都足以構成違憲。教育團體應儘速集結,向司法院聲請釋憲,讓大法官檢視制度合憲性,並加以修正。這不僅是為保護教師個人權益,更是為守護教育品質與尊嚴。
教師是知識的傳承者、價值的引導者,社會應給予尊重,而非讓他們在不透明制度中任人宰割。教師節本應尊師重道,卻因校事會議濫用而蒙陰影。唯有還教師清白與尊嚴,教育方能重拾信任,社會方能真正理解「無罪推定」非法律裝飾,而是文明社會基石。教師節的真義,應是致敬教育,而非為教育人員舉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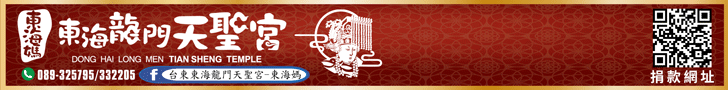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4416117_122148183224564414_2022793461796062593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75124989_122138600534564414_5098057897882802451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下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打造專屬成功模式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5825496_122150271926564414_9054305621568034742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962107_122147791340564414_6695923268119771423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邀約到場不是結束,而是成交的開始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024255_4003090606632661_4408849211036270947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想賺錢卻不想學?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1820331_122146449434564414_9052605497599197724_n-360x180.jpg)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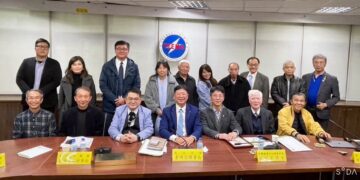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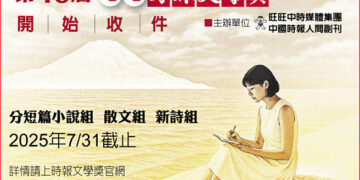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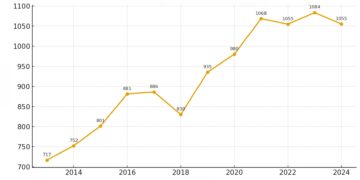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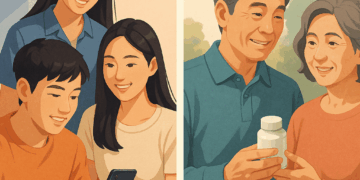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