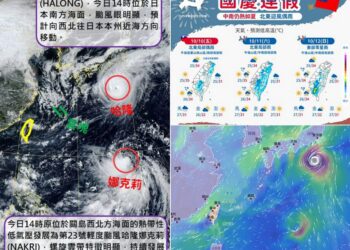文/李文煥
教改推行數十年,教育部高舉「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」與「快樂學習」的理想,試圖為臺灣學子擺脫聯考的陰影。然而,當我們拉開校園的帷幕,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幕悲劇:升學主義的迷思猶如鐵幕,不僅未曾消散,反而更緊地勒住了孩子們的喉嚨。這種迷思的共犯結構已然成形:家長篤信「孩子考好就是有成就」,教師則將「學生考好就是好老師」奉為圭臬。在這種單一、扭曲的價值觀下,無數具備多元潛能的好苗子,被無情地投入升學的機器中碾壓。我們必須直視:有多少孩子因為無法負荷這沉重的期望與壓力,最終選擇以極端的方式解決自己的人生?這才是真正的危機:是「有病的教師、有病的家長」,讓原本單純、正常的孩子們,在窒息的環境中逐漸生病。教育正常化,這個看似最基本的目標,為何至今仍是世紀難題?
單一價值觀的桎梏:對多數孩子的集體宣判
這種升學掛帥的思維,從學校的最高決策者到基層教師,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許多校長仍以國三生考了多少個 A 作為校務經營的最高成就,將榮耀聚焦在少數菁英身上。這不禁令人想問:在常態分配下,那八成以上不是頂尖成績的孩子,難道就不值得學校的肯定嗎?他們的多元天賦、善良品格、運動細胞,難道就不該被看見?當校園將成功狹隘地定義為高分時,它實際上是在對大多數孩子宣判:你們不是教育的成功品。這種價值觀的扭曲,為後續一切違規亂象提供了溫床,而最直接的體現,便在於變形的「第八節、第九節」輔導課。
變形的「輔導課」:從「零選擇」到「集體欺瞞」
地方行政機關的輔導辦法白紙黑字寫著:輔導課應「自由參加」、「不得提前講授新進度」。然而,這不過是教育現場一場心照不宣的集體欺瞞。首先,所謂「自由參加」已淪為「零選擇」。學校將輔導課美其名為「菁英班」,利用教師的引導和同儕壓力來驅趕學生。更惡劣的是,許多學校採取「操作性混蛋」的做法——將正規課程內容安排在第八、九節時段,迫使不想繳費或不想留校的學生,不得不屈從以避免錯失學習進度。其次,法規要求的「不教新進度」已然形同虛設。這不僅是個別學校的行為,更揭露了各縣市教育行政機關的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」。在「不這樣做就會落後」的集體焦慮下,多數學校選擇「陰奉陽為」來爭取升學優勢。面對教育部三令五申的「教學正常化」,所有參與其中的教師,無疑是成為了教學不正常化的幫兇,共同加劇了孩子的學習壓力。
教育倫理的崩塌:疲勞學習與雙重收費的爭議
當國中生一路從早上讀到下午五點半,已是第九節課的極度疲勞,這樣的學習還能有多少效率?教師們必須捫心自問,這背後驅動力究竟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效益,還是為了那份額外的輔導鐘點費?更可議的是教師的職業倫理。教師已領取國家支付的全額薪水,其中已涵蓋了對寒暑假期間的合理安排。然而,全國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舉辦寒暑輔,並向學生和家長額外收取「輔導費」。這是一種教育資源的雙重剝削。寒暑假本該是學生家庭教育、社會參與及身心休養的寶貴時光,卻被變成了老師的「外快」來源。我們不能讓學生和家長成為教育體制雙重收費的受害者,犧牲孩子的健康去成就這畸形的教學模式。
教改的最終目的,不該是分數的提升,而是人格的健全。許多好苗子不是輸在資質,而是輸在了這套只看成績、無視人性的升學機器下。教育部若真心想推動「正常的學習」,就不能任由地方教育機關在輔導課的議題上「掛羊頭賣狗肉」。改革不能只靠口號,必須從嚴格查處、懲罰違規學校開始。請讓國中生在下午四點準時放學,讓他們有時間去發展體育、藝術、社會責任,去享受一個正常的童年。否則,在這升學主義的巨大陰影下,所謂的「五育均衡」和「快樂學習」,將永遠只是一句空洞、且諷刺的口號,而我們將繼續收割的,只有被升學機器碾壓過後的破碎青春與生病的孩子。請還給臺灣的孩子,一個正常的國中教育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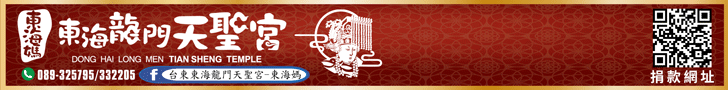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4416117_122148183224564414_2022793461796062593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75124989_122138600534564414_5098057897882802451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下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打造專屬成功模式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5825496_122150271926564414_9054305621568034742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962107_122147791340564414_6695923268119771423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邀約到場不是結束,而是成交的開始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024255_4003090606632661_4408849211036270947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想賺錢卻不想學?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1820331_122146449434564414_9052605497599197724_n-360x180.jpg)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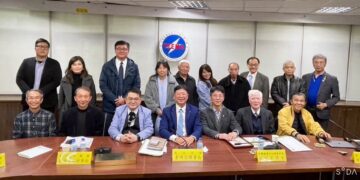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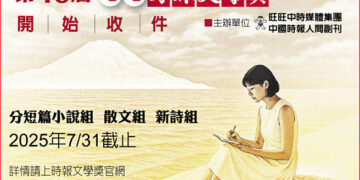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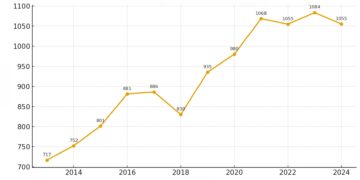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