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李文煥
近年來,台灣社會愈來愈常聽見一句話,從客家人口中被輕描淡寫地說出來,卻令人心驚——「我是客家人,但我不會說客家話。」
這句話說得太過自然,甚至顯得理直氣壯,彷彿不會說自己的母語,早已不是一種缺憾,而是一種可以公開陳述、無須解釋的身分狀態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說出這句話的人,往往並非全然不懂客語的年輕世代,而是仍然聽得懂、甚至曾經能說的中生代。他們不是不會,而是選擇了不說。
在社交場合,他們改用華語,因為那被視為體面而安全;與朋友往來,轉而使用臺語,因為那顯得親切而融入;談到孩子的未來,強調英語與外語能力,因為那象徵競爭力與前途。至於客家話,則往往能避則避、能省則省,甚至被視為一種不必要的文化暴露。有些人心裡明白,卻仍選擇沉默;有些人甚至相信,不說,才是聰明的生存之道。
這樣的選擇看似理性、務實,卻正在形成一種集體而持續的語言退讓。這並非外來政權的禁止,也不是制度性的打壓,而是一場從族群內部發生的語言自我消音。正因為它是自願的、安靜的,所以更深層,也更難被察覺。這樣的處境,不免令人想起一則西方寓言——模仿鳥的故事。
模仿鳥極其聰明,能模仿所有鳥類的叫聲,也能學動物,甚至學人類說話。牠因此備受讚嘆,被視為天賦異稟的存在。然而有一天,當旁人請牠唱出一段屬於自己的歌聲時,模仿鳥卻沉默了。不是因為害羞,而是因為牠早已忘記,自己原本的叫聲是什麼。這則寓言之所以令人警醒,正因為它映照了現實中某些正在發生的事情。
長久以來,客家族群被視為勤奮、聰穎、適應力極強的族群。為了生存、為了融入、為了不被邊緣化,學會他人的語言、配合主流的語言情境,成了一種必要的生活策略。然而,當這種策略逐漸內化為習慣,甚至演變為價值判斷,當「會說別人的語言」被視為能力與榮耀,而「使用自己的語言」卻被視為多餘甚至尷尬時,問題便不再只是語言流失,而是族群意識正在被悄然掏空。
語言一旦退出日常生活,便很難再回到核心位置。它不會突然消失,而是被慢慢擱置、逐步弱化,最後只剩下象徵性的存在。當客家話只出現在舞台表演、節慶活動或文化標示之中,而不再出現在家庭對話與日常交談裡,它的消逝,其實早已開始。最令人感到沉痛的,並不是外人聽不懂客家話,而是客家人自己逐漸不再想說、不再敢說,甚至不再認為「該說」。我們或許聰明地學會了更多聲音,卻也在不知不覺中,離自己的聲音愈來愈遠。
然而,自然界裡其實還有另一種鳥,提供我們截然不同的啟示。九官鳥同樣以善於模仿聞名,牠們能學習各種鳥鳴,也能模仿人類語言,但九官鳥並未因此失去自我。在同類之間,牠們依然使用原本的九官鳥叫聲彼此溝通。模仿,對牠們而言是一種能力;回到自身,則是一種本能。這樣的對照,不免令人反思:身為客家人的我們,是否還保有這樣的自覺?在他族面前展現語言能力也就罷了,但在同為客家人的場合,為何理直氣狀的講「我不會說客家話」?
當一個族群,連在彼此之間都不再使用自己的語言時,這已不只是環境使然,而是意識層面的退卻。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工具,它承載的是記憶、情感與歷史,是祖先留給後代最直接、也最脆弱的文化痕跡。當一個族群主動放棄自己的語言,也等於主動切斷了與自身歷史的連結。如果有一天,客家人仍在,卻只剩下身分標籤;如果有一天,客家文化只存在於展示與影像,而不在生活與對話之中,那麼,我們終將走向寓言中模仿鳥的結局。
客家鄉親們,我們或許精於學習別人的聲音,但不能因此失去自己的聲音。會說別人的語言,是能力;願意說自己的語言,才是尊嚴。客家人,請做九官鳥,切莫去做模仿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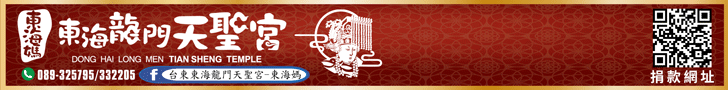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![[回顧報導]◆761休士頓客家會展現客家真情 在海外慶祝2014年天穿日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6/01/j20260128074852_o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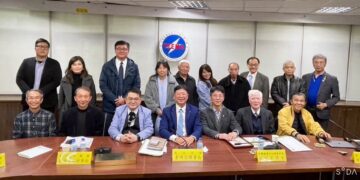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
-26-360x180.jpg)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![[回顧報導]◆761休士頓客家會展現客家真情 在海外慶祝2014年天穿日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6/01/j20260128074852_o-350x250.jpg)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