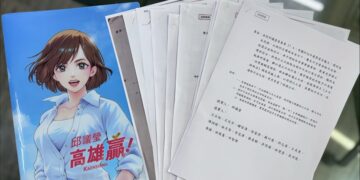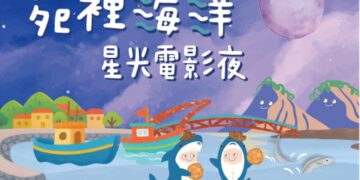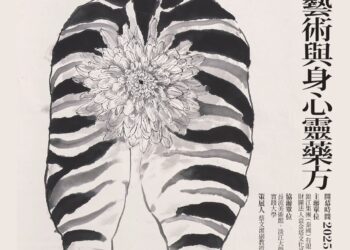文/李文煥
今日,客家摯友傳來一篇文章,談的是1986年新加坡一位部長鄭章遠的故事。他在貪污案遭調查期間,留下遺書,最終選擇服藥自盡。據報導,他在遺書中寫道:「作為一個有尊嚴的東方紳士,我覺得應以最嚴厲的懲罰贖罪。」字裡行間充滿懊悔與羞愧,宛如對天道與社會的深刻自白,令人不勝唏噓。
讓這段歷史廣為人知的,還有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冷峻回應——當鄭章遠向他求情時,他只回了一句:「我若幫你,新加坡就完了。」短短十字,道出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決心與制度的鐵律。這不是對個人的無情,而是對社會整體的負責;不是不念舊情,而是清楚制度不可容情的底線。
這段故事讓我深有感觸。回望台灣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發展,多少政要名流、地方大員在任內貪污收賄、圖利親信,卻能在事後全身而退。無論藍綠執政,皆不乏類似案例。有些人熟知法律漏洞,精於規避追訴;有些人善於操弄輿論,轉移焦點;甚至有些人在遭判刑定讞後,依然能逍遙於政商之間,遠走海外安享晚年,任憑人民在原地忿怒、失望,卻無從伸張。
這樣的現象令人不得不反思:我們的法律是否太容易被人「玩法」?我們的道德底線是否早已在一次次妥協中不斷下墜?更令人遺憾的是,小貪往往重懲,大貪反而輕放。基層公務員可能因為一盒月餅、一張餐券而遭記過、調職,而高層官員收受鉅額政治獻金、暗中喬事喬案,卻能以「政治追殺」或「程序瑕疵」為由,全身而退。
坊間曾有一種考驗人心的比喻:若在路上撿到100元,多數人會送交警察;若是一千元,也許會猶豫;但當金額成了一萬、十萬、甚至一百萬,道德就開始動搖了。然而,制度的設計,並非為了檢驗誰的道德較高尚,而是要讓人「不敢貪」、「無從貪」、「不需要貪」。這才是健康政治文化的根基。
佛教中有一句話:「因果不虛,業報不爽。」意思是說,人的行為都會留下業力的種子,無論善惡,終有果報。這並非是做一件好事就能抵消一件壞事,而是如同兩條平行的流水,善業和惡業各自流向其應有的結果。
因此,你今日捐款建廟、成立基金會,固然是積善之舉,但並不代表明日就可以貪污枉法,便能以此功德抵銷罪業。佛教認為,「功不掩過」,一件惡行仍需面對它的果報。善是善,惡是惡。錯了就是錯了。不該得的,就是貪。
然而在台灣,一種令人錯愕的生存邏輯卻悄然形成:小官不敢貪,因為風險太高;大官卻敢貪,因為涉案規模夠大、牽連夠廣,媒體焦點一過,政治風向一轉,真相就沉沒於塵埃之中。他們把人民困在國內的高房價、高物價與低薪結構中,自己卻能出國泡湯滑雪、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。人民在新聞前憤怒幾天,最終也只能無奈轉身,繼續為柴米油鹽奔波。
我們並不苛求每位政治人物都要像鄭章遠那般,以死贖罪。誠然,這樣的選擇未必是唯一的道德答案,甚至有人批評那是一種極端。但無論如何,他所展現的那份羞恥心與自我約束,是當今政壇中難得一見的精神資產。當一個社會的領導階層喪失羞恥心,無論制度如何設計、法律如何細緻,也只淪為紙上談兵。
筆者深信,法律或許能被操弄,輿論或許會被操控,但上天的審判絕對不會錯過。這並非迷信的報應觀,而是人心深處對正義最後的信仰。那是一種信念:是非對錯不可混淆,道德信仰不容讓價。
新加坡之所以能從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島,發展為今日廉政效率的典範,靠的從來不只是高薪,而是嚴明法治與全民道德共識的長期累積。若台灣真心想建立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,恢復人民對公共體系的信任,就不能再容忍那種「貪污,只要技巧高明就無事」的文化繼續蔓延。
是非有別,黑白分明,不該隨著權力大小而改變。不該得的,就是貪。莫以惡小而為之,莫以善小而不為。這不是口號,而是我們亟需重新拾起的信仰與底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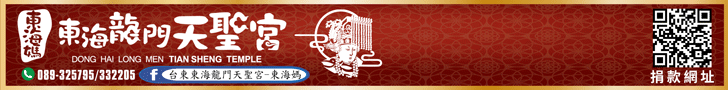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4416117_122148183224564414_2022793461796062593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75124989_122138600534564414_5098057897882802451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下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打造專屬成功模式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5825496_122150271926564414_9054305621568034742_n-360x180.jpg)
![[九型人格專欄]【上集】九型人格的習慣策略:掌握您性格類型的成功密碼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962107_122147791340564414_6695923268119771423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邀約到場不是結束,而是成交的開始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2024255_4003090606632661_4408849211036270947_n-360x180.jpg)
![[老鬼譚直銷專欄]想賺錢卻不想學?](https://www.worldviewnews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481820331_122146449434564414_9052605497599197724_n-360x180.jpg)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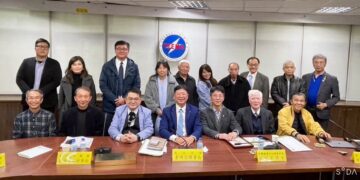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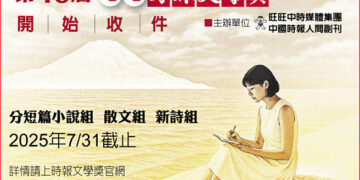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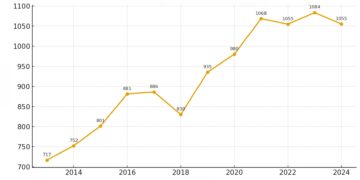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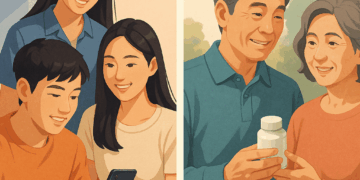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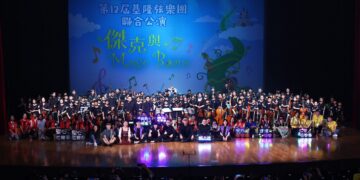

-360x18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欣賞謝德祥副總(右)在裝修業的專業實力,並認為天然防潮石膏磚)-360x180.jpg)